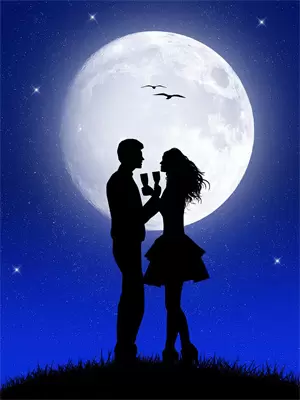1 叶落惊变我问你如何找到你,你说:“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。”庚戌年秋,鄂北清河村。
晨光熹微,东方刚泛起鱼肚白,一层薄霜覆盖着田野。院里那棵百年老槐树的叶子,
已黄了大半,风一过,便有三五片打着旋儿,轻飘飘地落到泥土里,悄无声息,
仿佛急着归根,为来年蓄力。屋里传来窸窣的动静,很快,炊烟袅袅升起。
男人脸上挂着掩不住的笑意,正用粗布擦拭着农具,对灶台边忙碌的女人说:“他娘,
今年这收成,咱家总算能过个肥年,娃娃们也能吃上几顿饱饭了!”莲子回头笑了笑,
眼角漾起细密的纹路:“是啊,爹娘在地下,也能安心了。”她口中的爹娘,
前两年饥荒时没能熬过来。“吱呀——”一声,院门被撞开,
三个孩子像小炮弹似的冲进院里,带起一阵风,将地上刚落的叶子又卷了起来,金黄一片,
煞是好看。“慢点跑!别摔着!”一个圆润温和的声音响起。门槛边,
一位身形富态、满头银丝的老太太,正扶着门框,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。这是胖奶,
村里最年长的老人,再过几天,就是她的113岁寿辰。在清河村,她就是一部活历史,
经历过三个朝代,如今是玄同二年。孩子们立刻围到她身边,叽叽喳喳地叫着“奶奶”。
胖奶颤巍巍地从深蓝色的粗布大襟衫口袋里,掏出几块用油纸包着的、有些融化的麦芽糖,
“来来来,奶奶专门给你们留的哩!”身后跟出来的两个中年汉子——大东和大阳,
见状想开口劝阻。大东嘴唇动了动:“娘,您牙口不好,这糖留着您自己……”话没说完,
就被各自的媳妇轻轻拉住。大媳妇莲子对大东摇摇头,低声道:“让娃们吃吧,娘高兴。
”二媳妇如花也拽了拽大阳的袖子,附和:“是啊大哥,这年头,有口甜的不容易。
”大阳看了眼媳妇,又把话咽了回去,他是个怕媳妇的,村里都知道。孩子们欢呼着拿了糖,
又跑开去撒欢了。大东大阳两兄弟,连忙上前,一左一右,小心地搀着胖奶回屋。
刚在堂屋那把磨得发亮的竹椅上坐定,天色骤然暗了下来。原本还透亮的天际,
不知何时聚起了厚厚的乌云,紧接着是滚滚雷声,由远及近,像是千军万马在头顶奔腾。
“不好!晒场的谷子!”大东惊呼一声,抄起墙角的木锨就冲了出去。
大阳和村里其他男人一样,像被火烧了屁股,抓起簸箕、扫帚,疯狂冲向村中心的晒场,
抢收那关系着全村人性命的粮食。女人们则赶紧关门闭户,安抚被雷声吓哭的孩子。
胖奶被安置在炕上,她浑浊的双眼担忧地望着窗外泼墨似的天空,以及那倾盆而下的雨幕,
嘴唇翕动,喃喃自语:“变天了,这回……是真要变天了……”那场雨,下得又急又猛,
仿佛要把天地都洗刷一遍。男人们拼尽全力,粮食虽抢回大半,却也湿透。夜里,
胖奶发起低烧,嘴里反复念叨着些模糊不清的词语,
什么“龙旗落了”、“新气象”……守在床边的大东和莲子只当她是烧糊涂了。第二天近午,
雨歇云散,天空碧蓝如洗,仿佛昨夜那场狂暴从未发生。大东端着一碗热粥,
轻手轻脚走进胖奶屋里。“娘!娘!起来喝点粥暖暖身子。”连唤几声,炕上的人毫无反应。
大东心下一沉,两三步跨到床边,伸手一探额头,一片冰凉,再探鼻息,已然全无。
他如遭雷击,僵在原地,手中的粗瓷碗“哐当”一声摔得粉碎。“娘!!!
”一声凄厉的哀嚎冲破屋顶,大东噗通一声跪倒在床边,这个顶天立地的汉子,
伏在母亲尚有余温的躯体上,嚎啕大哭。莲子、大阳、如花闻声连滚带爬地冲进来。
如花颤抖着手,触及胖奶冰凉的脸颊,眼前一黑,软软地向后倒去。大阳眼泪鼻涕糊了一脸,
慌忙扶住她,用力掐她的人中。莲子想去拉大东,手伸到一半,自己也撑不住了,扶着炕沿,
失声痛哭。孩子们的哭声、大人的悲声,混作一团。小小的院落,被巨大的悲伤笼罩。
就在这时,村长陈老栓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,听到哭声,脚步一顿,
脸上露出“果然如此”的悲戚。他顾不得安慰,冲进屋里,
对着沉浸在悲痛中的一家子喊道:“大东!大阳!节哀啊!赶紧的,把胖奶收敛了,
入土为安!然后……然后赶紧逃命吧!”他喘着粗气,
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惊惶:“南边……南边武昌出大事了!革命党造反了!
朝廷正调兵遣将地打呢!乱兵就快要波及到我们这儿啦!快走!往北走!”大东猛地抬起头,
眼睛血红:“我不走!我要守着娘!守着这个家!你们谁爱走谁走!”情绪激动之下,
他竟一口气没上来,晕厥过去。最终,在村长一家的帮助下,草草置办了一副薄棺,
将这位见证了百年沧桑的老人安葬在村后山坡上。村长找来一辆驴车,
载着昏沉的大东、哭哭啼啼的女人和孩子,以及一点 hastily 收拾的细软,
踏上了茫茫的北上逃亡之路。2 流离北城乱世之人,不如太平之大。他们以为北方是乐土,
殊不知,神州处处皆烽烟。一路上,所见皆是拖家带口、面黄肌瘦的流民,
路旁时有倒毙的饿殍。谣言与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他们盲目地跟着人流,也不知走了多久,
终于到达了一个相对繁华的城镇——北坪镇。这里暂时听不到炮火声,
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压抑。码头上、街道边,贴满了告示,有时是宣统皇帝的诏书,
有时是“民国军政府”的安民告示,老百姓看得懵懂,只知道城头变幻大王旗。
他们找到一处废弃的城隍庙角落安顿下来,大人孩子都已疲惫不堪,再也走不动了。
几个孩子,面黄肌瘦,依偎在一起,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和日晒,皮肤黝黑,
暂时只能给他们一个统一的称呼——“黑娃”。“饿……娘,
我饿……”最小的黑娃拽着莲子的衣角,声音微弱。大东和大阳对视一眼,咬了咬牙,
决定出去找点吃的。两人在这一天,融入了北坪镇为了一口吃食而挣扎求生的人流。
直到天快擦黑,两人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,脸上带着一丝庆幸,
怀里揣着几个杂面馍馍和一小袋糙米。“快,给孩子们弄点吃的。”大阳把东西放下,
招呼如花。莲子紧紧抱住大东,泣不成声,这一天,她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。
“俺这不是回来了吗?”大东轻轻拍着她的背,声音沙哑,“别哭了,
让孩子们看见……”正分着那点少得可怜的食物,村长陈老栓戴着破毡帽,
神色更加慌张地找了来。“这……这北坪也不太平了!”他摘下帽子,擦着脑门上的汗,
“听说袁宫保和南边谈不拢,还要打!咱们还得往更北边避避!”“还能去哪儿?
”大东闷声问,“俺今天在街上,听人说这叫‘国难’,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。
为啥……为啥就没人来管管咱们老百姓的死活?”他只知道,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,
都该让老百姓有饭吃,有活路。村长烦躁地摆摆手,点起一锅旱烟:“政府?朝廷?
他们顾着争权夺利呢,哪管咱们的死活!这战事不就是他们搞出来的?”他猛吸几口,
“俺们一家打算再往北,去滨州碰碰运气。你们……你们再想想吧!”说完,跺跺脚,
又匆匆离开了。村长走后,破庙里一片沉寂。大东蹲在墙角,粗糙的手指插进头发里,
一动不动,像一尊雕塑。莲子把一个温热一点的馍馍塞到他手里:“他爹,吃点东西,昂?
”“咱们走。”大东突然抬起头,眼中布满血丝,却有一种下定决心的光芒。“啊?
”莲子一愣,“还能去哪?不都说是国难吗?哪里不乱?”她不解,
但还是习惯性地支持丈夫,“不过,俺既然跟了你,就是你的人,你说去哪,俺就去哪。
”“我去跟大阳他们说。”大东起身,把莲子按坐在草铺上,“你看好黑娃。
”他走到用破席子隔开的里间门口,站在那儿,听着里面隐约的啜泣和低语,久久不动。
然后,他深吸一口气,掀开帘子走了进去。“大阳,咱们……”话卡在喉咙里。
他看见大阳和如花正慌乱地把一些东西往一个包袱里塞。“哥……哥,怎么了?
”大阳停下动作,眼神闪烁地看着他。“你们这是……要走?”大东的心猛地一沉,
快步走到他们面前,“什么意思?要分开走?”如花把包袱往身后藏了藏,强笑道:“大哥,
村长都说了这不安全,咱……咱也得为自己想想不是?
总不能一棵树上吊死……”她用力扯大阳的袖子。大东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头顶,指着大阳,
声音发抖:“亏我这个做大哥的,什么时候都想着你们!逃难一起,有吃的先紧着你们!
你们现在……现在要自己跑?”说着,他失控地一拳朝大阳挥了过去,结结实实打在他脸上。
大阳一个趔趄,嘴角渗出血丝。莲子听到动静冲进来:“大东!快住手!
”她上前死死抱住丈夫的胳膊,对吓呆的如花喊:“如花!你还愣着干啥!
”如花这才反应过来,也上去拉架。兄弟俩像两头被激怒的困兽,扭打在一起,
压抑了许久的恐惧、委屈、愤怒,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最终,以两人的鼻青脸肿和力竭告终。
莲子看着这对鼻青脸肿的兄弟,眼泪止不住地流,
她捶打着大东的胸膛:“你们这是要干啥啊?!娘才走多久,
你们就……就这样……”她看着垂头不语的两人,心灰意冷,“如果……如果确定要这样,
那咱们现在就分吧!分家!各过各的!”“分家”二字,如同惊雷,炸在每个人的心头。
这意味着,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,血脉至亲,从此各奔东西,生死由命。
“嫂子……”大阳捂着脸,瓮声瓮气地喊了一声,心里涌起巨大的悔恨。
大哥大嫂一直照顾他们,他却……如花还想争辩什么,莲子直接打断,
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冰冷:“不用说了。你们既然决定了,就走吧。休息好了,
带上你们的东西,走。”她搀扶起大东,不再看他们一眼,“起来,地上凉。”玄同二年,
冬。二十年的手足之情,在这个寒冷的北坪城隍庙里,宣告破裂,天各一方。
3 殊途分家后,大东和莲子带着对黑娃的无限愧疚,继续北上。
他们听说更北边的北城机会多些,或许能活下去。一路艰辛,抵达北城时,已是次年春天。
玄同帝已然退位,华夏民国的牌子挂了起来,但城里的气氛依旧微妙。他们一无所有,
只能从最苦最累的活计做起。大东有力气,去码头上扛过大包,
去建筑工地做过小工;莲子则给大户人家浆洗衣物,或者做些针线活。后来,
一位看着憨厚的老乡,开了家早点铺,缺个帮手,见大东肯干,便雇了他负责炸油条。
莲子也在铺子里帮忙打杂。生活依旧清贫,但总算有了个稳定的落脚点。
除了日常开销和偿还初来时欠下的债务,偶尔还能攒下几个铜板。
他们渐渐习惯了这座城市的喧嚣与冷漠,只求平安。民国元年12月20日,
北城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。莲子裹紧身上单薄的棉袄,朝手心哈着白气,站在早点铺门口,
看着雪花飘落。“大东,下雪了。”她回头对正在油锅前忙碌的丈夫说,
“也不知道……黑娃他们,现在怎么样了。”分家前,迫于生存压力,他们和大阳如花商量,
将三个孩子托付给了一户据说家境尚可、想要儿子的人家。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。
大东动作顿了一下,把炸得金黄的油条捞出来,沥着油:“黑娃们有福,
那户人家看着是厚道人。咱们……咱们自己都顾不过来,就别太担心了。”这话,
不知是在安慰妻子,还是在安慰自己。他催促道:“你快进去吧,外面冷,别冻着了。
”“掌柜的,油条好了没?等半天了。”有客人催促。“来了来了!刚出锅的,您趁热吃!
”大东赶紧把小筐递过去,脸上挤出一丝生意人的笑容。而在另一边,分家那天后,
大阳和如花带着分得的一点微薄钱粮,决定不再往北,转而向南,
试图回到相对熟悉的鄂豫交界地带。他们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,或许战事很快平息,
他们还能回到清河村。然而,现实无比残酷。在南下途中,他们遭遇了溃散的清兵抢劫,
混乱中,大阳和如花被人潮冲散,彼此失散。更雪上加霜的是,一直带在身边的三个黑娃,
也在那次混乱中不知所踪。大阳像疯了一样,在附近寻找了数日,喊哑了嗓子,踏破了鞋,
却一无所获。妻子不见了,孩子丢了,哥哥也决裂了。巨大的绝望和自责将他吞噬。
他漫无目的地游荡,不知该去向何方。一天,他流落到两省边界的一个小镇,
听到一群穿着灰色粗布军装、戴着红星帽徽的军人在演讲。他们宣传“打土豪,分田地”,
“打倒列强,除军阀”,“为了穷苦人打仗”。这些话,像一点火星,
落入了大阳早已冰冷死寂的心田。他想起了逃亡路上的饿殍,
想起了被抢走的最后一点活命钱,想起了失散的妻儿,想起了胖奶临终前“变天了”的呓语,
甚至想起了哥哥大东那句“为啥没人管我们”的质问。“俺参加!”大阳拨开人群,
走到招兵处前,眼睛里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芒,“俺要当兵!为俺娘、俺媳妇、俺娃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