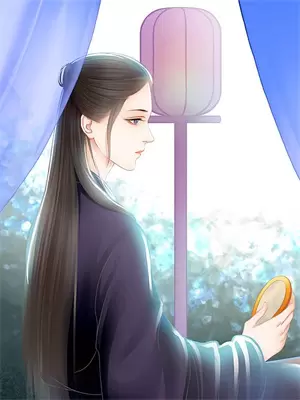天宝末,长安雨夜,代书人沈砚接下了一桩邪性买卖:仿写一封“亡妻”遗书。润笔,是五百两买命的官银;真相,是卷入权阉构陷忠良的泼天阴谋。
笔能杀人,墨可诛心。从被动卷局的棋子,到以笔为刃的弈者,他深入虎穴,周旋于帝国最危险的权谋旋涡。在真伪笔迹间设下致命陷阱,于滔天巨浪中搏一线生机......
长安夜雨,多是温吞黏腻的,唯独今夜,雨挟肃杀,砸在青石板上,声声砸碎人心。
我,沈砚,长安西市一介代书。
案头这桩生意,却很邪性。
三更锣歇,铺门无声自开。
一股龙脑香风先至,冲散满室墨臭。
来人玄氅曳地,不沾半点雨渍,将一只紫檀木盒轻放案上,威压如山。
“代笔。”
斗笠下嗓音低哑,“一封亡妻遗书。”
我刚要报价,他“啪”地掀开盒盖——烛火摇曳下,满盒官铸足色银铤,银光刺目。
整整五百两贡银,非权贵近臣不可得。
这哪是润笔,是买命钱。
“照此誊写。”
他推过一张素笺,字迹工整却匠气,“不得增减一字。”
我低头应允。
铺纸研墨,笔锋落处:“妾身林氏晚卿,自感时日无多……”
行至“林晚卿”三字,腕骨猛地一僵——墨滴坠纸,晕开狰狞污迹。
这名字,是淬毒的钥匙,骤然撬开我尘封的记忆:
恩师林敬之,前朝议大夫,三年前以“通敌蕃将”罪满门抄斩,唯此女下落不明!
通敌蕃将……当朝谁与蕃将牵连最深?
唯有威震西域的安西节度使。
而当年力主弹劾恩师的,正是权相杨国忠一党。
我强压惊澜,抬眼试探:“敢问……这位林姑娘,是府上何人?”
他置于案上的指节微不可察地一蜷,声线骤冷:“做好份内事。”
我噤声续写。
这遗书字字泣血,句句含情,俨然深情妻子对夫君的诀别。
可字里行间,我只嗅到浓烈的阴谋血气。
末句更是刺眼:“夫君待我恩重如山,妾身此生无以为报,唯有来世再续前缘。”
恩重?
对罪臣之女何来恩情?
除非这“恩”,是见不得光的交易!
书成。
他携书没入雨幕,如鬼似魅。
独坐至天明。
拈起一锭白银,底部刻铭赫然:安边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——河北道贡银,由杨国忠把控,唯内侍省高宦可动用!
的确,内侍省!
是那些伴君侧、握天权的阉宦!
一介代书,一卷伪书,一个手眼通天的宦官。
我接下的,是一张无声的催命符。
我必须找到她。
不仅为告慰恩师,更为自救。
自收下那官银起,我已成局中子,命悬一线。
巳时,依遗书所载,寻至城西宅邸。
寻得二楼一座雅座,正好可以看到林府侧门。
跟小二要了一杯清茶,楼里传来秋娘吟唱声,唱的正是乐府吴声小曲“春江花月夜”。
我很喜欢,这是张若虚写的。
小二拎着铜壶添水,茶水已经续了三次,日头已压着瓦檐。
此时,见晚卿素衣竹簪,自侧门匆匆而出,似在躲避什么。
正欲尾随,却见茶楼里糖葫芦小贩正在注视晚卿。
而这小贩也尾随着晚卿向远处走去。
其腰间衣袍下,隐有硬物凸起。
晚卿,你究竟是笼中囚鸟,还是……专为谁设的香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