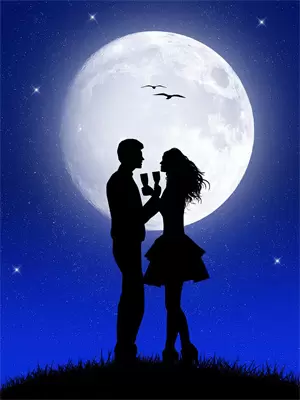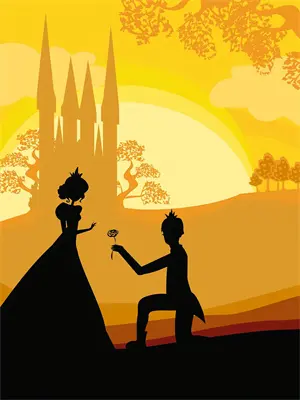
林承宇的指尖悬在碗沿,那处微微翘起的釉面,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生涩的光。
他的手指终究没有落下,只是无意识地摩挲着自己左腕上那道十公分长的疤痕。
疤痕是粉白色的,像一条僵死的虫,匍匐在麦色的皮肤上,
提醒着他三年前那个改变一切的午后。窑炉炸裂的巨响,飞溅的碎片,
以及随后父亲在赶来途中中风倒下的消息,这些碎片常常在不经意间拼接起来,
切割着他的梦境。工作台上,那只釉碗静静地立着,裂纹如蛛网,
在细腻的青花下游走、延伸,构成一幅他无法解读的绝望地图。“又失败了。
”他的自语声飘散在满是泥坯和半成品的工作室里,被一种更庞大的寂静吞噬。
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陶土、矿物釉料以及经年不散的窑火气息,这是他的城池,
也是他的囚笼。门轴发出极轻微的“吱呀”声,被人小心翼翼地推开。宋雨宁站在门口,
手里提着一个便当袋,身影被走廊的光拉得细长。她的脸色是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,
仿佛上好的白瓷,薄得能透出光来。然而,她的嘴角却像往常一样,
弯着一个温柔的、勉力维持的弧度。“看你灯还亮着。”她说,声音轻软,
像羽毛拂过寂静的水面,生怕惊扰了这满屋沉睡的瓷器和他紧绷的神经。承宇没有回头,
但他紧绷的肩线几不可察地松弛了一分。他能从脚步声中分辨出是她。雨宁走近,
目光越过他的肩头,落在工作台那只釉碗上。那些蜿蜒的裂纹,在她看来,
竟有种惊心动魄的美丽,像是大地干涸后自然的龟裂,承载着一种无奈又倔强的生命力。
“我带了香菇鸡丝粥,是你常去的那家,还热着。”她打开便当盒的盖子,
温热的蒸汽“噗”地腾起,瞬间在他们之间制造了一小片迷蒙的雾障。这人间烟火的暖意,
与这间充斥着矿物和火炼气息的屋子,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调和。承宇终于转过身。
他的眼底有血丝,是长期熬夜和心力交瘁的印记。他伸手去接勺子,
指尖带着长期接触粘土和釉料的粗糙感,此刻却有些不听使唤地微颤着。
几滴滚烫的粥洒在了沾满釉料的工作台上,留下几个深色的圆点。“小心烫。
”雨宁极其自然地接过勺子,俯下身,轻轻地搅动着碗里的粥,她的动作流畅而熟悉,
仿佛这个为他吹凉食物的动作,早已融入她的骨血,成为了一种无需思考的本能。
她低下头时,几缕柔软的发丝垂落,不经意间扫过承宇的手背。那一瞬间,
两人都像是被微弱的电流击中,微微一颤。这触碰太轻,太短暂,
却在他们各自的心湖投下了石子。“你看这裂纹,”承宇的目光像是被磁石吸住,
又回到了那只碗上,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被反复挫败后的沙哑,
“温度、时间、釉料的浓稠度……我核对了无数次笔记,
明明每一步都严格按照曾祖父留下的规程,可为什么……就是不对?”雨宁凑得更近些,
仔细端详着。她的视力极好,或许是因为右耳听力不佳,
上帝补偿般地赋予了她更敏锐的视觉。她能看清每一道裂纹细微的走向,
看清青花色在裂纹边缘微微晕开的痕迹。“我倒觉得这裂纹很美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
却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承宇心湖,“它们让这只碗活了过来,有了自己的记忆和故事。
就像生命本身,看似破碎,内里却蕴含着一种完整的、不可复制的历程。”承宇摇了摇头,
眼神固执而黯淡。“你不明白。曾祖父做的青花渗彩,釉面光洁如镜,温润如玉,
青花的边缘会自然渗出一圈紫金色的光晕,像是黎明前,天际那一线最难以捕捉的霞光。
那是活的,有呼吸的。而我做的这些……”他顿了顿,喉结滚动了一下,“永远是死物,
永远差着那么一点灵魂。”“差在哪一点呢?”她问,明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,
却依旧想引他说出来。说出来,总比闷在心里发酵成苦毒要好。“不知道。”他闭上眼,
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,“若是知道,早就解决了。有时候我觉得,我和曾祖父之间隔着的,
不只是时间。”雨宁沉默了片刻,走回自己的包旁,
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、皮质封面的笔记本。她翻到用淡紫色书签标记的一页,
指尖点着上面娟秀的字迹和手绘的图表。“我今天在市档案馆,
查到一些关于你曾祖父当年烧窑的杂记。里面提到,他用的釉料基底里,除了常规的原料,
还有一种特殊的草木灰,是取自老窑房后面那棵百年槐树,
只在特定时节采撷的槐花和嫩枝烧制而成。笔记里说,那槐树的年纪,比瓷厂还大。
”她抬起头,目光清澈地看着他,“承宇,那棵槐树,在你小时候,厂区扩建时,
就被砍掉了。”承宇猛地睁开眼,怔在原地。这个消息像一把冰冷的凿子,
瞬间击碎了他长久以来赖以支撑的某种信念。他张了张嘴,
声音干涩:“所以……是因为这个?所以,我永远也做不出一模一样的青花渗彩了?
”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攫住了他,仿佛他这些年的所有努力,都是在向着一个海市蜃楼奔跑。
“也许,”雨宁合上笔记本,声音轻柔得像一声叹息,“我们不必追求一模一样。
”她的话音未落,一阵压抑不住的咳嗽突然从喉咙深处涌了上来。她猛地转过身,背对着他,
单薄的肩头因为剧烈的咳嗽而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,像风中无助的落叶。
这咳嗽声撕破了工作室的宁静,也终于拉回了承宇沉浸在瓷器世界里的全部注意力。
他皱起眉,带着几分不确定问道:“你……感冒了?最近好像总听你咳嗽。”咳嗽渐渐平息,
雨宁深吸了几口气,才转回身,脸上努力挤出一个宽慰的笑容,摆了摆手:“没事,
就是有点累,可能最近换季,着了点凉。”然而,在工作室昏黄的灯光下,
她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,几乎看不到血色,那是一种不健康的、令人心悸的透明感。夜深了,
雨宁缩在工作室那张旧沙发上,身上盖着承宇之前给她的一条薄毯,似乎睡着了。
承宇却毫无睡意,他坐在工作台前,手里捏着一块素坯,却久久没有动作。
他的目光不时地飘向沙发的方向。雨宁的睡颜很安宁,长睫在眼下投下淡淡的阴影,
右耳侧的头发散乱地贴在脸颊上,随着她平稳的呼吸微微起伏。
他忽然想起她刚来厂里不久时,有一次闲聊,她曾指着自己的右耳,
用一种近乎轻松的语气说:“你知道吗?七岁那年一场高烧,
这里的听力就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了。”当时她还笑了笑,那笑容里有淡淡的遗憾,
但更多的是一种奇异的释然,“因为听不清,我反而学会了用眼睛更仔细地看这个世界。
看云的变化,看叶的脉络,看人脸上最细微的表情……有时候我觉得,我‘看’到的,
比很多人用耳朵听到的还要多,还要真实。”现在,看着她在睡梦中毫无防备的样子,
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,像冰冷的藤蔓,悄无声息地缠绕上承宇的心臟。
他说不清这恐慌源于何处,只是觉得眼前这幅静谧的画面,脆弱得仿佛一触即碎。凌晨三点,
雨宁从浅眠中醒来。 studio 里只亮着一盏孤零零的台灯,
承宇不知何时已趴在工作台上睡着了,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也是微蹙着的。
她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他的深色外套,
上面还残留着他身上特有的、混合着陶土和松烟墨的气息。她轻轻起身,拿起外套,
小心翼翼地披回他的肩上。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,却依旧固执地绷紧着。
她走到工作台前,目光落在白天那只开裂的釉碗上。裂纹在冷白的灯光下,显得更加清晰,
也更加无助。她静静地看了许久,然后,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,她拿起一支极细的画笔,
在调色盘里蘸了少许青花料,俯下身,屏住呼吸,开始沿着那些天然的裂纹,
极其细致地描绘起来。她的手腕稳定,笔触轻盈,碎裂的纹路在她的笔下,
逐渐演化成了一株苍劲的梅枝,旁逸斜出,疏落有致。那些原本象征着失败的裂痕,
此刻竟完美地融入了画面的骨理,成为了构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恰到好处,宛若天成。